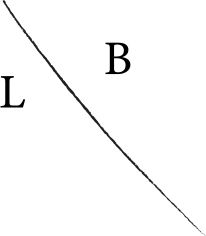破碎的尘殇--关于陆斌的艺术
冯博一
艺术家陆斌的创作,给我的感觉一直是与主流艺术保持着“疏离”的“边缘”关系,其生存状态颇为内敛、低调而另类。上世纪90年代在深圳时,我们就很熟悉,后来他去南京艺术学院任教,与前卫艺术的喧嚣渐行渐远。也许他不愿意卷入现实的狂欢,而希望在“混世”里求得一份心灵纯净的觉知与体验。但他的这种疏离、边缘或另类,不是如上世纪90年代许多在野艺术家的“被边缘”,而是一种自愿或主动地选择,一种介乎于其间的自由,且若即若离地独立姿态。当他最近将一些近年的作品拿出来的时候,我对他的这种认知就更加明确了。其实,陆斌一直没有闲着,只是有意远离所谓的中心,心无旁骛地创作与教学。陆斌的艺术始终是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化、当代性导致的诸多问题进行不断地实验性转化,具有明确的现实文化针对性。他主要以陶瓷、陶土、紫砂等材料作为媒介,以装置等多媒介方式关注于历史、记忆、城市化等问题意识,如《大悲咒》、《化石》、《都市》等一系列的创作。
长久以来,我们总是说中国文化是“历史的、辉煌的”。然而,现在的中国文化却很难再说是“历史的”了。因为“昨天”刚刚过去,并被迅速遗忘,甚至有意篡改、摧毁。不用多久,有关昨天的记忆可能就会成为忘却干干净净的“白茫茫一片大地”。在《大悲咒》中,陆斌通过陶瓷烧制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佛塔、佛经文献、青花器皿等,以及将其逐渐破碎化的过程,针对和所表现出来的是历史的模糊、信仰的丧失殆尽、文化无所归属的现状。他在一种社会历史与现实的表征中,将标示历史、信仰的佛塔建筑被坍塌的过程,多媒介地任意地混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陆斌的艺术方式。倘若将这种独特性与中国以往惯常的现实主义相比较,是否可以看作他艺术的方法更多地带有后现代现实主义艺术的色彩?后现代现实主义艺术既保持了现实主义纪实的传统,又揉合了现代主义艺术中常见的自我意识和前卫艺术实验性与批判性的特征。即陆斌的这些作品有着逼真的外表,而作品本身的情境和叙事语境对这种逼真性又进行了颠覆,从而解构了我们的历史记忆,并以其中的过程反映了他的对历史与现实的态度与立场。
而《化石系列》在我看来是一种重构历史、指涉现实的转化方式,既超越了一般写实性作品“一对一”视角的泛滥,也超越了作为建筑、物质的单一功能和性质,成为记录时间、历史和生活本身的痕迹标示,甚至直接对应和测度着现实的沧桑变化。或许这就是陆斌将陶瓷作为媒材,凝固不同历史阶段的代表性典型性符号整合的过程,而构成他完整作品在视觉上的朴素、纯粹和消解的内在力量。有形的器物在陆斌这些作品中,被无形的碎片渐变为废墟的场景,恰恰是我们在现实生存状态的一种真实写照的隐喻与象征,也显示出他的这种不露声色“尘迹”的沉寂,洞察与表现的力度。换句话说,他没有把对时间、空间的表达限制在记录的层面上,他也不满足于把媒介转换为一种视觉语言,而是他把这种景观沉淀为“尘殇”的底色,把现实着眼点对准了历史、文物以及最为自然最为日常的景与物之上,并透过时光的浮尘去发现、思考我们习以为常的现实处境。这应该是艺术表现历史、重构记忆、置换现实的重要表现方式之一。
虽然破碎,但陆斌的作品本身的呈现又拥有一种完整性,它基于历史与现实,同时又有所超越。在东方文明中,佛塔被视为宗教、信仰的永久纪念物,不仅蕴含着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特定文化,也表征了人类寻求自身存在意义的漫漫征程。他烧制、破碎的方式,也是与虚构式书写相对应的史学书写,两者组成了陆斌这些系列作品的复调。这种纯艺术与拟史的复调象征了作者复勘历史与记忆的方式,它使艺术上升到主体,而使历史背景退居到注脚的位置。因此,陆斌艺术语言所表达的意义,不仅在于用一种新的视觉观念和手段表现我们这一代的文化记忆,还在于为我们记录了精神和情感的历史。同时,较为特殊的是陆斌一直以陶瓷的这种承载着中国文化传统的符号材料作为主要媒介,使他深切地体验到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轮回演绎。他是通过现状来追溯它曾经的历史“辉煌”和当下的“颓败”,由此揭示出中国历史传统本身的弊端,批判锋芒直接指向我们历史的盲目性。显然这有借古喻今的意味,更有着对现实的警醒作用,以及对未来预知的焦虑。而这一切都是以陆斌的反思性追问加以表达的。在这个意义上,陆斌的作品无疑是对历史的哀悼,对艺术与美的祭奠。是为“尘殇”的语义与寓意。也许历史是无尽的,它永远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因而,不断地“燃烧”才成为可能,也才能够接续我们的记忆和历史的情怀。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变动的一个主要变化,外在的也是内在的深刻变化是中国人所谓的“改天换地”。改朝换代也同时意味着改天换地,意味着从空间着手展开的权力巩固与再生产。对于物质的改造与生产,既直接展现了历史的变化、社会的变迁、权力的运作,也反映了各个时代中人的空间意识与空间意志的变化,以及加诸于空间、寄托于空间之上的权力志向、欲望、想象以及美学趣味等。在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城市”越来越成为艺术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城市化不仅被认作为一种现代化的表意符号和物质定向,亦被预想为一种催生新的人文机制和价值系统的媒介。但是,现代都市从来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巨大悖论,带给人们的常常是交织着痛苦与欢欣的复杂情感。一方面,都市文明以物质的形态向人的生活方式全面渗透,还蓄蕴着一种我们过去未曾经验却代表着历史、文明进步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都市的这些物象又是一种冷漠的拒绝。现代都市无一不是充满着欲望、病态、罪恶与丑陋,它已经用自己的隐形之手,将其塑造成一个压抑人的庞大的异己的存在。特别是在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都市人的心理层面上,更充满了诱惑、错愕、焦虑的不平衡状态。对这种状态的质疑是当前一些艺术家创作“城市性作品”的观念前提和可利用的创作资源,亦清晰、明确地敷染在陆斌作品所创造的“都市”系列文本之中。他在《都市系列》作品中,关注现实生活的具体性,致使一种日常生活的特色呈现出来。从而在现代性宏伟叙事中被忽略和压抑的日常生活趣味变成了艺术表现的中心,赋予了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日常生活再发现的进程,以及通过对于日常生活的组合拼贴,将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和消费的价值被凸显出来,历史和个体生命的运行就被赋予了越来越大的意义。这并非是传统人文主义式宏大“主体”的展开,而是一种个人生存实在经验的体现。因为,文化不是或不仅是成规范的现实,也不仅仅是被长期沿用的符号系统或既已存在的意识形态固定下来的观念和解释,而更多的是鲜活灵动的原初状态下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文化形态呈现的不仅是一种结果,更是一个过程。也许远离喧嚣的现实使陆斌的艺术保留了寓情的细末微节,凸现了他作品的质感,我们在观看他的作品时常常会遭遇到这样的细末微节。他是从现实的个人经验中剪裁物质的碎片去释怀他的记忆、爱好和趣味。
中国这个充满混杂的碎片化时代,不知所终地将把我们带向何方的现代化过程,使一切都变化的急速而扑朔迷离。在一个仍在不断转型的时代里,事物是那样的复杂,许多边缘都变得模糊。人的价值观、信仰、欲望、相互间的交往、权力的运作,包括我们以为透彻的金钱关系其实都并非那么清晰可辨;人与人之间,性别的中性化,甚至倒错,情感的无法划分定位,造就了我们漂浮的缺乏节制的游离状态。相对应于“碎片化”是身处我们这个时代个体共同的视觉与心理体验。当被击碎的信念、信仰,以及价值系统消散为历史和时代尘埃之时,抑或还是会以新的方式重构?在当下,身处多变的时代涡流,更需要我们重启对于未来的关注与想象。恰如美国马歇尔·伯曼教授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周宪译)一书中的观点,因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